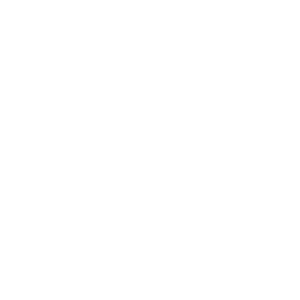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阿达·约纳特(Ada E. Yonath)
Yonath 1939 年生于耶路撒冷。1962年和1964年,Yonath 分别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化学理学学士学位和生物化学硕士学位;1968年,她获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X射线晶体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1969年)和麻省理工学院(1970年)从事博士后研究。她在1970年组建了以色列第一个蛋白晶体学实验室,早在2006年,Yonath因在“核糖体蛋白合成,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领域中获得突出成就,获沃尔夫化学奖。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表彰除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外,对于化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它是化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2009年10月7日,Yonath同美国科学家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托马斯·施泰茨共同获得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化学奖,其中Yonath是自1964年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科学家。
Yonath 年近八旬,却依旧光彩亮丽。她的性格十分活泼,访谈中妙语连珠,展现了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记者:此次能请到您,是我们莫大的荣幸。请问我院是如何与您取得联系的?吸引您来参加这次论坛的原因是什么?
Yonath:我收到了王新生院长的E-mail,很高兴他在信中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特色。我到过北京、上海、重庆、厦门,可还没有来过青岛。青岛是个很漂亮的城市,我很喜欢这里。
记者:我们很期待您能再到青岛来,与我院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Yonath:在中国,我正与厦门进行关于伤口愈合方面的合作项目,如果今后有机会,我很愿意与青岛合作。
记者:我们将不胜荣幸!作为1964年后唯一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女性,请问您在科研方面有何心得?您组建了以色列第一个蛋白晶体学实验室,领导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请问您在女性领导力方面有何经验?
Yonath:我觉得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男女都是一样的。科学对任何人来说都任重道远,都需要严谨的态度、艰苦的努力和敬畏之心。你看(打开电脑为我们展示其科研团队成员照片),我的科研团队的大部分成员是女性,我不觉得女性和男性在科研和领导力方面有何不同。我希望人们把我作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待。
记者:您已经75岁了,仍然保持着这样旺盛的科研精力,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
Yonath:我今年29岁!
记者:您对科研付出如此多的心血,请问您如何协调科研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Yonath:我爱科学研究,也爱我的家庭。如果你爱它们,你自然知道如何去平衡它们。
记者:能为论坛提点建议吗?您的建议对我们很重要。
Yonath: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与会经历。接待我的孙明姝大夫及志愿者对我的照顾十分周到,各方面的组织和服务都让我觉得很贴心。或许下次会议你们可以把每位演讲嘉宾的讲稿都翻译成中文,让更多英语不好的听众得到更详细的信息。我觉得增进语言沟通十分必要。中文太难了!你们怎么做到读写这些汉字的?
韩国延世大学医疗集团CEO郑南植、外科教授李宇政
延世大学医疗集团始建于1885年,目前主院区由癌症医院、康复医院、心血管医院、眼耳鼻咽喉医院、儿童医院、牙科医院、国际诊疗中心及达芬奇培训中心共同组成。除了位于新村地区的主院区外,另有江南Severance医院、龙仁Severance医院、Check-Up体检中心等分支机构。Severance医院是韩国最早的一家现代化医院,在韩国最早通过JCI认证和再认证,也是保持JCI认证地位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医院。自1996年开始,我院与延世大学医疗集团正式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双方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项目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两大医疗集团的深入交流。
记者:郑院长,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延世大学医疗集团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应用情况?
郑南植:我们医院2005年开始第一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现在有6台达芬奇机器人。到去年底我们已开展了一万多例手术,是全世界开展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数量最多的医院。
记者:在这一万多例手术中,如何?
郑南植:具体数据请李宇政教授介绍一下。
李宇政: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创口更小,手术效果更好,可以说是99%。其实那1%并不是说手术失败了,而是有一部分原本准备进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患者后来被发现还是更适合开放手术,于是我们将患者转去做开放手术。对医生来说,患者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为了追求百分百的让患者接受并不合适的手术。
记者:我们医院刚刚开展了第一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请问李教授能否对我院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开展提一些指导意见?
李宇政:医生在操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之前多进行腹腔镜手术会有很大的帮助。达芬奇机器人的操作和开车很像。我们都知道开车的时候只有你对车熟悉,有熟练的驾驶技术才能顺畅行驶。同样,在开展手术之前,医生需要十分熟悉机器人,熟练操作流程,才能顺利开展手术,保障手术效果。
记者:延世大学医疗集团与我院一直有密切合作。除了达芬奇机器人之外,今后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合作?
郑南植:从1996年开始,青大附院和我们医科大学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2001年开始,青大附院外科与我院外科开始频繁接触,双方每年都互派人员进行交流。你们大外科主任吴力群、胆道外科副主任孙传东的博士学位就是在延世大学取得的。他们都是十分优秀的医生,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除达芬奇之外,我们希望在心血管、脑血管、癌症、脊柱外科等学科继续开展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
记者:延世大学和青岛大学都是庞大的医疗集团。我们的医疗集团由多个医院联合组成,不知延世大学医疗集团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
郑南植:和青大医疗集团不同,延世大学医疗集团由大学和医院两部分组成。延世大学由护士、牙科、医科、保健分属大学组成,同时还有几家Severance医院。所有这些合称“延世医疗院”(延世医疗集团)。我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30年前,1885年延禧大学和Severance医院合并,取双方的前两个字组成了今天延世大学的名称。在韩国也有青大附院这样多个医院联合形成的医疗集团。各个医疗集团的组织架构不同,但都有各自良性运转的体系。
记者:您下午参观了我们医院,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郑南植:虽然很想到四个院区都走一走,但由于时间紧张,我们仅仅参观了院本部。在院本部,我感受到青大附院的历史积淀,看到诸多等待就诊的患者。通过这些,我可以感知到青大附院培养出了一代代优秀的医生,造福了无数患者。我始终认为历史对医院来说至关重要,青大附院能有今天的发展规模,与深厚的历史积淀息息相关。在这个基础上,青大附院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记者:这一点也和延世大学医疗集团很像。
郑南植:是的。
记者:针对本次论坛,能留下您的宝贵建议吗?
郑南植:首先我要祝贺你们这次高峰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论坛涵盖了医疗行业的多个热点主题,让不同领域的听众都能获得最有效的信息。不知今后你们是否可以再举办一些癌症、心血管、脑血管等单个学科的论坛?这样会造福专攻这些学科的医生和科学研究者。
美国妇产科学院院士、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Diane C. Bodurka
Bodurka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生活质量、病人疗效报告、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其他卫生服务研究。她负责了很多生活质量和卫生服务研究以及卵巢癌新疗法的临床试验。Bodurka博士目前是美国妇癌科T32号补助金支持项目“妇癌科学术培养”的联合负责人,这个项目是妇癌科负责的两个卫生研究所补助金支持项目之一。
Bodurka博士积极参与国家学术活动,加入了妇科癌症学协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她是美国妇科癌症学协会的委员会成员、卫生服务研究小组主任以及布兰顿-戴维斯卵巢癌研究项目执行委员会成员。她高超的临床技能和对患者的付出为她赢得了美国最佳医生、休斯顿最佳医生以及美国顶尖癌症专家的称号。
记者:十分荣幸能邀请到您参加本次论坛。
Bodurka:贵院的陈爱平教授曾经在我们中心访学,参与了中心的许多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次也是陈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论坛的,非常感谢她。
记者:能否请您简要谈一谈您在这次论坛上的报告内容?
Bodurka:我的报告首先提供了国际卵巢癌及生活质量研究的最新进展的介绍,包括一些临床分析,历史数据及最新研究结论;此外介绍了一些卵巢癌治疗方面的新方法。
记者:您的科研成果丰厚,能否请您对我院青年医生提一点指导意见?
Bodurka: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掘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从我确定自己的兴趣点在卵巢肿瘤治疗方面后,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热情。有了兴趣和热情,才有克服困难的动力。
记者:能为论坛提点建议吗?我们希望把下一届办得更好。
Bodurka:非常棒!论坛的组织和服务都让我感到非常亲切舒适,和各位嘉宾及与会者的交流互动也非常愉快,真的很棒!
记者:如果有合作机会,您希望在哪些领域?
Bodurka:其实除了科研工作之外,我还负责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培训工作,我期待今后能有机会与贵院在人才培养工作上互通有无。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于金明教授多年来工作在肿瘤放疗临床、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率先在国际和国内开展了肿瘤的立体定向、适形、调强放疗,影像引导的放疗,生物学靶区,分子影像学和基因增敏等多项代表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研究工作。他在突破制约放疗疗效的两大瓶颈——精确施照和精确靶区勾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现阶段开展肿瘤精确放疗新技术、新方法的开拓者之一,曾获得2010年度山东省科技最高奖,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记者:于院士您好!您是我们医院的老朋友了,欢迎您!
于金明:你好!上个月我刚刚参加了贵院市北院区的开业仪式,非常成功。这次论坛,我接到了贵院梁军副院长的邀请。应该感谢青大附院举办了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医学论坛,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加深合作的平台。此次参会专家的规格之高、分布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可以说在省内是不多见的。我虽是主讲者,却也是抱着学习者和参会者的心态来的。
记者:您作为国内肿瘤专家,如何看待我院肿瘤医院的成立?是否考虑今后与我院在肿瘤诊疗和科研方面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动全省肿瘤学科发展?
于金明:贵院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综合技术力量日益增强。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我想,肿瘤医院的成立也是建立在贵院这所百年老院的深厚根基上的。肿瘤医院无疑是贵院发展肿瘤优势学科的重要举措,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不论是青大附院还是山东省肿瘤医院,都要抓住发展契机,找准发展方向,加快人才和学科建设。只有内外因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我们与贵院也将继续在肿瘤学科上加深合作关系,加强指导,互相帮助,互促提高,合作共赢。
记者:您本次的讲座主题是“肿瘤个体化治疗进展”,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下肿瘤个体化治疗的背景吗?
于金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放疗设备和技术费用都在不断翻番,但晚期癌症患者存活率并未明显提高。那么,该如何突破癌症治疗手段上困局?个体化治疗就此应运而生。个体化治疗就是针对肿瘤患者亚群,结合他们在临床、病理以及分子生物学上的不同特性,采取不同手段,为他们达到最大疗效和最小身体伤害。具体可以分为群体个体化和个体个体化。比如,中国人的食管癌90%是鳞癌,是因为热的食物刺激,美国人的食管癌90%是腺癌,以贲门癌为主;中国的肝癌大多是乙肝引起的,美国的肝癌是酒精肝引起。病因不同,在治疗上也截然不同。而患者的个体化差异就更多了。人身体的生物多态性会导致各种不同的症状出现。就像喝酒,有人喝一口就不行了,有人喝半斤也没事,这就是个体化差异,是因人而异的,要从基因的角度去判断。
记者:您在去年设立了总额为500万元的“于金明院士科技创新基金”,奖励在医疗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人才,这一举动的初衷是什么呢?
于金明:在我看来所有的成果都是集体科研的结晶。一花独放不是春,在抢占学科至高点的同时,更要形成一个队伍链条,这样才能保证长久的竞争力。为了鼓励团队的发展和创新,我们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就是想凭借人才优势和科技实力打造一所一流的肿瘤医院。
记者:作为国内知名肿瘤学专家,您能谈一下肿瘤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于金明:科学没有终点,你向前走着走着就会进入到一个盲端,但无论如何你毕竟是接近了目标。肿瘤方面,现在不知道的、等待研究开拓的领域太多了。我认为,基因检测及个体化治疗将会带来新的治疗理念的变化,也会为治疗手段的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
格里菲斯大学健康研究分子与基因医疗部主任魏明谦
魏明谦教授1983年毕业于原青岛医学院医学系,1986年获山东大学微生物硕士学位,1993年获西澳科廷科技大学生物医学理学博士学位,1992至1993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12月至1996年5月任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基因治疗及相关技术研究,是世界知名基因传递和治疗,特别是癌症基因治疗专家。他致力于微生物载体系统开发,发表同行评论120多篇,在澳医学界、政界享有较高声誉。
记者:魏教授,我们从您的简介中了解到,您之前有一项研究课题“让细菌杀死癌细胞”,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魏明谦:肺癌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癌症,在发病早期难以诊断,75%以上的患者到晚期时才被确诊。由于传统方法*可能性低,不能渗透固体肿瘤,所以我们设计了一种细菌,它能像导弹一样发现肿瘤,渗透到肿瘤组织内部释放出能抑制肿瘤生长的特定因子。这一研究结果可应用于90%的固体癌症,我们将这种新细菌命名为“特洛伊木马”。
记者: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所工作的学府?
魏明谦:格里菲斯大学成立于1971年,目前共有学生43000多名,办学规模在澳大利亚排第九位。格里菲斯大学也被视为澳大利亚最具创新精神和在亚太地区影响最大的高校之一。另外,格里菲斯大学附属黄金海岸医院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医院。
记者:此次论坛上,您与我院肿瘤分子与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签署了合作协议,之后将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呢?
魏明谦:我们将重点在肿瘤研究与临床交流方面展开长期合作,我将到贵院进行讲座,同时贵院也将派遣人员到我们的实验室培训。相信我们双方合作将会非常愉快。
哈佛医学院教学院长David H. Roberts:作为医生要加强终身学习
本次论坛上,哈佛医学院教学院长David H. Roberts作了《加强终身学习》的演讲。David结合当下的医疗状况和大数据时代形势,介绍了哈佛医学院的办学理念以及正在开展的全球培训项目。
哈佛医学院的历史可上溯到1782年。1810年,哈佛医学院在波士顿正式成立;1906年,校址迁至郎福德大街。哈佛医学院曾在世界医学历史上创造过4个“首创”:率先引入胰岛素;发明人工呼吸机;开发牛痘疫苗;成功完成首例肾脏移植手术。目前哈佛医学院已建立起“哈佛医学院社区”,包括波士顿儿童医院、剑桥健康联盟、福赛斯学院、哈佛皮尔格林医院等17所教学医院。目前这个哈佛医学院的“世界班”共有12337名教师,9个院系,却只有708名医学博士生,915名理论博士生和180名医学双博士生。
David提出,大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改变,医疗服务理念和方式应随之而变,这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医生需要加强终身学习,不断在教育技术、内容、发展和贡献能力上投资,而医学院也必须为医生的终身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在未来的100年里,对医学院来说,成功的人才培养意味着需要在教学、研究及临床治疗上全线革新,并具备抓住机遇的能力,掌握打破壁垒的方法,拥有卓越的领导力,以及借助先进教育技术的能力。
哈佛医学院正致力于并用传统和新兴工具教学法,为全球的终身学习者提供健康、疾病、科学、临床诊疗及研究方面的教育机会。目前,哈佛医学院设有“世界临床学者研究培养计划”、“在线学习平台”、“院长教育计划”等多个项目,并正在扩大全球教育服务。除临床研究培养外,2015年,哈佛医学院还将提供医疗质量安全与信息、世界癌症治疗、实验方法以及发展新型治疗法等方面的相关培养。哈佛医学院每年提供超过250个直播课程,开拓在线平台进行远程教育,以实现未来“即时到达”的学习要求。展望未来,哈佛医学院将发展重点放在振兴生物医学研究、通过新的合作模式促进转化医学发展,并欲在全世界拓展哈佛医学院的声音。